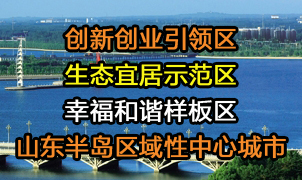
“拿医院的事情当自己的日子过,医院才能办好;把医院的同事当自己的兄弟姊妹看,医院才能管理好;拿病人当自己的亲戚朋友照顾,病人才能恢复好。”这是潍坊市优秀共产党员、诸城市龙都卫生院原院长王金鉴的“三好理论”。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扎根基层34年,先后担任4个乡镇卫生院院长,不忘初心,任劳任怨。遗憾的是,他的生命却在50岁时戛然而止……
7月初的诸城龙都卫生院,夏意正浓,湿热的空气里夹杂着凄切的蝉鸣。
300多天前,这所卫生院的院长王金鉴躺在病房楼里,和病痛作着最后的抗争。他在用残余的精力和信念支撑自己,盼着女儿大学录取通知书早日到来。
妻子迟永萍看着他发白的面庞、颤抖的嘴唇,心如刀绞。怎奈苍天无情,2015年8月9日,他带着对妻女的无限憾疚离开了人世……
改革先拿妻子开刀,第一个下岗
收拾完60平方米的小屋,迟永萍关上风扇,闭合好门窗。过滤掉外界的干扰,她才能安下神来,回忆道:“金鉴脾气很犟,认准了一件事,就下决心要把它干好。”
王金鉴是乡镇卫生院业务的多面手。16岁时,他到程戈庄卫生院工作。在那里,他做了20年药剂师,双手如秤,抓药可以做到分毫不差,人送外号“黄金手”。
从2001年起,他先后在桃园、辛兴、百尺河和龙都4个乡镇卫生院担任院长。相对于那些大医院,乡镇卫生院是名副其实的小院、土院,那时乡镇卫生院普遍不景气,通病很多:硬件较差,一屁股外债,病人不来,连职工工资都发不下来。
王金鉴数次临危受命。首先是在桃园,那时的桃园卫生院可谓“火坑”。
火从何来?地处山区的桃园卫生院,条件简陋。王金鉴接手时,石块和垃圾散乱堆在院子里,药品摆放得乱七八糟,墙缝中有数处老鼠洞,患者挤在脏兮兮的小平房里。附近群众说起桃园卫生院,大多摆手摇头,难言满意。
和丈夫一起来的迟永萍见此景,心里难免咯噔一下。与其说是卫生院,不如说是杂货场。即便如此,她依然留下来,在卫生院的药房里记账,照顾结婚十多年的丈夫。
对着眼前的脏乱,王金鉴找来铁锨筐兜,默默干了起来。几个年轻职工看到满头大汗的王院长,也纷纷加入。石块和垃圾被清理完毕,连老鼠洞也被塞上水泥,卫生院的面貌焕然一新。
外表干净了,内里更得明净。王金鉴发现有的职工人浮于事,对患者冷淡,想灭掉这团怪火。可从哪下手呢?思来想去,只有拿自己人开刀,让妻子迟永萍第一个下岗。
“他说不能搞特殊化,家属坚决不能留下来。”迟永萍虽满腹委屈,也只得收拾铺盖卷回老家,独自拉扯着女儿,靠打打零工应付生活。
接连送走四五个浮于工作的职工后,王金鉴开始思忖如何把流失的患者请回来。他常对职工们说,也每每反问自己:“基层卫生院就是为基层群众服务的。群众的需求是我们存在的价值,如果群众都不来看病了,卫生院还有什么存在价值?”
人命至贵,有贵千金。王金鉴深知良医难求,他骑着那辆老式二八自行车,到40里外的诸城市区一家家医院跑,苦口婆心劝专家到桃园坐诊。慢慢地,来桃园卫生院求医的人多了起来。
2003年的辛兴卫生院,更是谁都不愿碰的烂摊子。群众“大病不敢来,小病不愿来”,职工工资发不出,卫生院濒临解体。职工们灰心丧气,没了精气神,要么天天混日子,要么找门路赶紧走。
40多人的辛兴卫生院,只剩下20来人,这些职工也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
辛兴卫生院副院长王术鹏还记得第一次见王金鉴的场景——
“一个普通中年人,个头不高,夹着破包,穿着旧夹克。他缓缓走到卫生院,四下张望,瞅瞅这看看那,我们还以为是新来的司机,没想到他是新院长,是来帮大家脱困的。”
辛兴卫生院复兴的希望押在新建门诊楼上。可后续资金迟迟不到位,门诊楼被迫停工半年之久。为此,王金鉴到处借钱,好不容易筹集了资金。
盖楼时,王金鉴像给自己家盖房子一样,每天蹲守在工地上。他精打细算,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,连废钢筋、水泥袋子都攒起来,甚至还学会了刷浆和刷漆。
“我早上给他皮鞋擦好鞋油,过几天回来衣服皮鞋上,全是油漆和涂料,整个人就像头小土驴。” 迟永萍回忆起那段岁月,嘴角浮现淡淡微笑。
半年的少眠无休,换来了三层门诊楼的完工。卫生院的职工有了奔头,再也没人提调离的事情。
走进王金鉴的办公室,屋顶装有一台锈迹斑斑的吊扇,吱吱悠悠地一圈圈转着,屋内燥热异常。摆放着的桌椅、沙发、书柜,样式陈旧,一眼看出年头不短。
这办公室内所有家具,竟是王金鉴厚着脸皮从诸城市区一家医院手里“抢救”出来的。原来,市区一家医院搬迁,废弃的家具,被他当作宝贝拉了回来。
辛兴卫生院职工们记得,王金鉴在辛兴呆了5年6个月零7天,留下1200平方米的门诊楼、2600平方米的病房楼、2300平方米的后勤楼和3500平方米的职工宿舍楼。
宁肯累自己,见不得别人吃苦受累
卫生院逐步好转,王金鉴的白头发却日渐增多。“他经常说苦点累点没关系,等将来好了就都好了。”迟永萍至今仍难掩心酸地啜泣道。
迟永萍心里一直想着“将来好了”赶紧来。她和王金鉴曾有一个可爱的儿子,养到五岁时因患先天性心脏病夭折。孩子重病期间,夫妻俩每晚轮流抱着呼吸困难的儿子,彻夜不眠。
儿子夭折后,同事们从未见过王金鉴掉过一滴眼泪,总像没事人一样,在医院里忙前忙后。可有一次,一个同事打扫卫生时,忽然看到从王金鉴的书里掉出一张小孩的照片。待她弯腰捡时,王金鉴以快她几倍的速度捡起来锁到了抽屉里。王金鉴的眼圈红红的,泪水涌上眼角。
生离死别让迟永萍更渴望团圆。哪怕是在租来的小窝里,一家人也能其乐融融。
可希望越热切,失望越剧烈。2003年的11月,王金鉴罕见地早早回家,迟永萍既惊且喜,为此还多准备了几道小菜。王金鉴提起筷子,给妻子夹了几口菜,平淡地说:“俺要上辛兴卫生院了。”
饭菜尚温,迟永萍的心却有些凉。她了解辛兴卫生院,那里条件差、人心散,在诸城卫生院中排名倒数,没人愿意去。她心里一百个不愿意,可还是鼓起勇气问:“咱不去成吗?”
“上级让我去哪,我就去哪。我是党员,就应该冲在前面。”王金鉴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一夜未眠,两口子彼此无言。第二天一早,王金鉴打点好了行囊,义无反顾地走了。
“他刚上辛兴那会儿,正是最难的时候,十天半月不回家。我记着那年冬天格外冷,我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买不上煤,孩子就捂在被窝里写作业。”“女儿那时候小,小手捏着铅笔冻得通红,哆哆嗦嗦地问我:妈,人家都有爸爸,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爸爸啊?”
迟永萍盼周末,等到过了下班的点,却只等来一个电话:“临时有事情要处理,不能回家了。”其实,那晚王金鉴本来兴冲冲要回家,可周末大家拼车回家,车满坐不下,他让别人走了,自己留下来。
“2004年快过年了,我生病,好久没有看到金鉴。除夕那天,下午五点多,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见面了。我看到他的衣服也皱了、头发也白了,满身泥水和油漆,像逃荒回来似的,我俩一下子抱在一起。我在他怀里使劲哭。”迟永萍回忆当时的情景,眼泪扑簌直下。
“永萍啊,以后会慢慢好的,我暂时顾不上你们,我会好好补偿你们的。”一句拙朴的话,让迟永萍娘俩又过了一年。一起走过这么多年,迟永萍知道丈夫王金鉴宁肯苦自己、累自己,都见不得别人吃苦受罪。尤其是他所在的卫生院,服务的多是农村的贫苦百姓,生活更加不易。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力量,为农村医疗、为百姓做更多的事。
刚到辛兴卫生院时,院里有一排低矮破旧的平房,作为值夜班职工的宿舍。王金鉴把好房间让给别人,自己住最差的一间。房间大门正对着高约3米的仓库,盛夏湿热深冬刺骨。迟永萍来辛兴看望丈夫,看到床上单薄的被褥,眼泪就扑簌簌地往下掉。
为改善职工的住宿条件,王金鉴盖了一栋家属楼,自己也分到了一套房子。王金鉴当了好些年基层院长,可一家人一直居无定所。
“我和他先住在程戈庄卫生院宿舍,后来租了房子,再后来住在亲戚的房子里,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家。”知道王金鉴分到一套住房,迟永萍高兴得几晚睡不好觉,不顾丈夫劝阻执意要去辛兴看看新房子。
到了卫生院,迟永萍才知道,丈夫已将家属房腾出,让给了一位外地专家,自己搬到顶层的办公室了。
“我埋怨他,觉得他太不爱惜自己身体。原来的宿舍条件太差,上面掉土,下面返潮,住在那里让我难受。现在好不容易分套房又给让出去,他怎么就这么傻?”
王金鉴只是笑笑,眼睛眯了起来,安慰妻子住哪其实都一样。
“人活着是要吃饭,但绝不是为吃饭而活着”
“其实都一样”是王金鉴常挂在嘴边的话,卫生院职工们听得耳熟。
“他在吃穿住行上从不讲究,大家提意见,他就用其实都一样来解释。”辛兴卫生院财务科长王娜娜说。
有时候半夜三更做手术,他就像病人家属一样等在外面,一直等着。手术结束了,职工们疲惫,他也熬红了眼圈,但是一清早他就到街上买来小米粥和油条,嘱咐大家多吃点。
可他自己却过着苦行僧的生活。王术鹏还记得,王金鉴将一些馒头片放在太阳底下晾晒的情景——
把买来的馒头切片摆在日光下,晒干了制成馒头干。平时吃饭时,用水一泡,兑点咸菜就是一顿饭。大家劝他改善改善生活,他总是说:“不就是顿饭嘛,饱了就行,人活着是要吃饭,但绝不是为了吃饭而活着。”
他和单位司机一起出差,别人从衣着上把司机当院长,把他当司机。有人劝他做院长要注重仪容外表,王金鉴又说,穿啥其实都一样。
在卫生院,王金鉴有一辆“专车”。他把车让了出来,作为卫生院的班车。班车接送职工、接送患者,就是不接送院长。“院长的车是手术病人专车,那会儿乡镇公路坑坑洼洼的,颠得厉害。病人在我们院里做了手术,出院的时候院长让用院里唯一的桑塔纳轿车送病人回家,轿车舒服,不会扯得刀口疼。”王娜娜说道。
2009年6月,王金鉴从辛兴调到百尺河卫生院。“他来的时候,没人想到他竟是这么好;他离开的时候,交接会上大家哭作一团。”辛兴卫生院副院长蒋红梅说。
王金鉴到任之初,蒋红梅到百尺河的亲戚家做客。亲戚边招呼边兴致勃勃讲:“从你们辛兴调来一位好院长,百尺河医院变得很不一样。”
蒋红梅非常惊讶,王院长才调任不久,竟又忙碌了起来。蒋红梅转念一想,其实到哪都一样,这不就是那个闲不住、总想干事创业的王院长嘛。
半年之后,上级考虑王金鉴与家庭聚少离多,将他调到龙都卫生院。龙都卫生院毗邻市区,条件较好,调任此处是对王金鉴的照顾和关怀。
王金鉴还是停不下来,他首先控制辅助检查的费用,降低药品价格,减轻百姓的就医负担,将公共卫生服务落到实处。
在龙都,王金鉴每天主持晨会,总是第一个来。卫生院办公室主任向王金鉴建议:“院长,现在很多单位都用指纹机点名,要不咱也买一台?这样您就不用每天都到会议室点名了,再说机子也不贵。”
王金鉴语重心长地说:“点名是次要的,我主要想利用点名的机会,把我发现的问题指出来,把我的想法传递给大家,我要让大家心往一块使、劲往一处拧。”
打开龙都卫生院的电话号码簿,扉页上便是王金鉴生前亲笔撰写的《职工修养十二条》:1、看一个人的操守,在其利益得失时;看一个人的度量,在其面临喜怒哀乐时……9、坚持以德修身,境界提高了;坚持业务学习,专业功底扎实了;肚子里装得东西多了,才能做到厚积薄发,少犯错误……
王金鉴的“三好理论”
“爱人如己是大哥的天性。”王金鉴的弟弟王金明说道,哥哥是家中老大,十多岁时就推着小车到城里面粉厂换面,为家里买油买菜,“过年的时候,爹娘忙年没时间赶集,都是大哥带着我和二哥去买过年的衣裳,买一毛钱三十个的小爆竹,他自己却舍不得花钱买点啥。”
“每次我们兄弟聚在一起聊大哥的工作时,他就说:拿医院的事情当自己的日子过,医院才能办好;把医院的同事当自己的兄弟姊妹看,医院才能管理好;拿病人当自己的亲戚朋友照顾,病人才能恢复好。”王金明谈及大哥的“三好理论”。
在程戈庄卫生院,一位在家破膜的临产孕妇,胎位不正、脐带绕颈2周,必须马上剖腹产,可当天手术包已全部用完。王金鉴马上电话联系周边乡镇医院,自己骑着摩托车借来手术包。手术期间,王金鉴一直在手术室外陪家属聊天,缓解家属的焦虑。
辛兴镇山东村伤残军人刘淑臻,复原后定期到辛兴卫生院诊疗。2003年11月,初任院长的王金鉴看到因病痛折磨而心情不佳的刘淑臻,正和值班大夫闹情绪。王金鉴主动上前和老人聊家常,了解老人在战争中腿部受伤截肢,子女不在身边心情甚为苦闷。
王金鉴经常抽时间陪刘淑臻聊天,掏钱帮买饭、打水。有一次王金鉴外出培训,他怕天冷路滑老人外出不便,就给同事100元钱扛回两箱大碗面,以备不时之需。后来,老人不光看病找他、换假肢找他、家里有难题也找他,把王金鉴当作亲人。
2009年6月,王金鉴调任百尺河卫生院,刘淑臻就跟到百尺河。2009年12月,王金鉴调到龙都卫生院,老人又跟着过去。
有人问刘淑臻:“老大爷,王院长又不看病,您在辛兴看病好好的,为啥总大老远来找他呢?”“俺信他”,刘淑臻三个字的回复让许多人动容。
在辛兴卫生院盖门诊楼时,王金鉴总泡在工地上。他看到一名拾荒者经常在工地附近休息,便拜托他在自己外出时照看工地。拾荒人说到做到,王金鉴大为感动。王金鉴了解到拾荒人无儿无女,便常带着生活用品去看望老人,聊聊家常,老人孤寂的晚年生活有了一丝温暖。老人逢人便说,自己就没见过这么没架子的好干部。
“他挨个病房转,有窗户透风,第二天他就修好了。那时候他睡觉也不多,晚上就一个人围着医院转悠。”王术鹏说道。
“有一次,在门诊大厅里,一名40多岁的病人家属发现身上仅有的120元钱丢了,心疼地大哭。王院长问清原因后,安慰她说,钱找到了,快别哭了。其实,在场的好几个同事亲眼看见王院长从自己兜里掏出了120元钱,塞给她付医药费。”王娜娜回忆道。
在龙都卫生院,打扫卫生的职工管明彬冬日衣衫单薄瑟瑟发抖。王金鉴看到后便拿出300元钱,悄悄嘱咐两位工作人员给老管买件过冬御寒夹克。老管拿到衣服,老泪纵横。
在王金鉴家里,家里妻子管钱,他一个月给家里300块钱。迟永萍知道,他把钱又花在病人身上了,“可能他天生就是那种有悲悯情怀的人吧,看不得别人遭苦遭罪。”
“再给我十年,我会让我的人生更完美”
龙都卫生院病房楼竣工后,王金鉴回家的频率高了起来,迟永萍再一次看到“好日子来了”的希望。
然而日积月累、忘我的工作,使王金鉴积劳成疾。2014年11月,他自己成了患者,被诊断为肝癌晚期。
王金鉴向医院请了半月假到上海治病。“在大医院住院期间,他还了解人家医院的管理模式,琢磨人家哪里值得学习。临上手术室了,他还拿着手机拍医院的宣传版画。”王金明说大哥完全忘掉了自己是个重病患者。
可不到10天,他自感时日无多,执意要回到工作过的龙都卫生院。刚到诸城,他就回到医院参加考勤大会。在晨会上,他向大家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汇报自己关于工作的点滴看法。台上声音时断时续,台下同事一边听,一边担心着自己的院长。
住院期间,他还关心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改革,身体一有起色,就向主管领导说说自己的想法,希望自己的建议能为新医改提供一些借鉴。在弥留之际,王金鉴对前来看望他的同事说:“假如上天再给我十年时间,我会让我的人生更完美!”
“我尽心尽力,无怨无悔,这辈子值了,只是对闺女有亏欠,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。”病床上,王金鉴和迟永萍说着心里话,表达自己的歉疚。
“他一直在等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,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,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。”迟永萍说道。
因家里经济条件有限,父亲治病又欠下将近十万元的医药费,在填报志愿时,女儿填报了西南和西北的学校。旁边人问她为什么这样选择,她说:“我爸爸治病欠了不少钱,西南和西北地区消费低,我选的专业学费也低一些。”
后来,在家人的劝说下,也为了以后更方便照顾母亲,女儿选择了青岛的一所大学。她的父亲清贫了一辈子,她知道,父亲给她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……

